听叶嘉莹精妙阐说
- 时间: 2017-07-21 09:07
- 作者: 姚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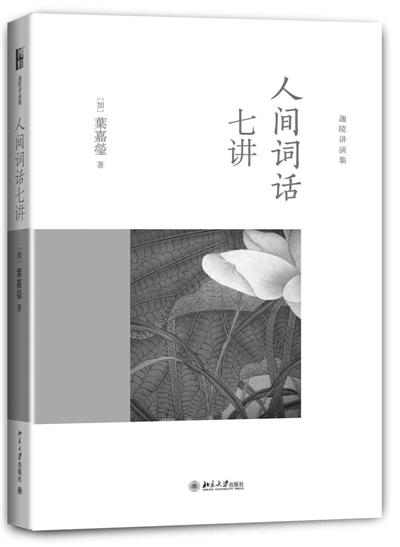
闭门向山路,深柳读书堂。 思思 作
作为入选“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”的《人间词话七讲》,是王国维、叶嘉莹两位词学大师的一次跨世纪精神合作。叶先生对王国维及《人间词话》的演绎,让读者离这部文学名著更为亲近。对经典的敏锐洞察,对东西方批评理论的融会贯通,对多方话语的辨析与尊重,植根于深厚底蕴的独到见解,使得本书文字典雅、情致生动,古今中外旁征博引、通达自如,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与赏析开拓了全新的视野。
倘若再观古典诗词在中国的生存境况,耄耋之年的叶嘉莹先生不知是否倍感欣慰?时下大众对于诗词学习的热度高涨,令人振奋。当年,对于古典诗词在年轻人中的传承状况,叶先生曾是颇为痛心的,称之“如入宝山空手回”。她曾对学生言道:“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、智慧、品格、襟抱和修养。诵读古典诗词,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。”诗词不死,心灵不死。这也可视作叶先生与古典诗词相伴一生的写照。
出身书香门第的叶先生自幼扎下良好功底,求学辅仁大学之时,师从学者顾随,顾先生对诗歌“跑野马”似的不受条框局限的讲授,对叶先生影响深远。顾老师对这个学生的期望是“别有开发,能自建树”,而叶先生也果真做到了“今天讲的也是自己的东西,不是老师讲的”。叶先生1945年大学毕业就开始教书,今朝年过九旬的她,在讲台上“和诗歌谈了一辈子恋爱”。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盛赞叶先生讲解诗词“阐说精妙,启发无穷”。
之前读过叶嘉莹先生的《风景旧曾谙》一书,仿佛是一条古典诗词赏析的纵贯线,以时间为序,从上古一直讲到晚清,宛若大河奔流。而此次捧读《人间词话七讲》,则是聚焦在一个个点上的探幽析微,从一个细微落点的引入和打开,让人深深感受到了叶先生的治学精要。在叶先生的娓娓道来中,满目所见,尽是芳华。多变的视角和落点,使得读者对古典诗词的理解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丰富的想象。无论纵向梳理还是横向切入,无不尽显功力。
所以选择《人间词话》,也可视作叶嘉莹先生和王国维先生跨越时空的心灵相印。在《人间词话七讲》的开篇就已可见叶先生对于王国维的推崇,直指现在很多读书人对于学问的功利,他们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学问,是“学问的外表”。王国维呢,叶先生论道,王国维追求的已不仅是真正的学问,而是真理。叶先生对王国维的推崇可见一斑。于是,与其他讲解迥然有别的是,叶先生对于王国维的评析居然是从哲学意味上展开的,有此作者与讲者的契合做底,叶先生对于《人间词话》的解析,从中也可窥得叶先生自身的治学风范。推崇归推崇,在批评一道上,叶先生是严整犀利的。
对经典的敏锐洞察
《人间词话七讲》开篇即对全文的起始点予以质疑。《人间词话》第一则第一句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:“词以境界为最上”。恰恰就是这“境界”二字,叶先生认为不妥,“从开始,王国维就给大家带来混乱了”。众所周知,“境界”二字是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中最叫得响的观点,堪称经典。叶先生偏生就在经典上开始较真。她的观点是:诗词曲赋莫不讲求境界,以此指为词所特有,并不精准。当然,她还是很给王大师留了余地的,她认为王国维是没有说清楚,并不是没有弄清楚。王国维只是找不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词来表达罢了。即使是批评也极有分寸,可见先生修养。
随后,她进一步指出,王国维所用例证诸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“寒波澹澹起,白鸟悠悠下”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“落日照大旗,马鸣风萧萧”都是诗而非词,“诗中不是也有境界吗?你为什么说只有词以境界为最上呢?”找到问题不是目的,解决问题才见功力。之后的几讲中,叶先生尝试运用“添字注经”的办法,力图讲清楚“境界”这个词,或者换言之,试图把王国维所领悟到的那个东西表达清楚。全书中类似的质疑,都建立在对文本细究始末的严谨态度上,并未因研究对象是公认的经典而生了妄自菲薄之心。
对东西方批评理论的融会贯通
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分析,叶先生东西贯通,居然引入西方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意识、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概念,来诠释创作中的无意流露。有意思的是,在叶先生的解析中,“断章取义”是一个正面的文学解释方法——不管全诗说的是什么,只取这两句或几句的意思,这就是每个人的眼光所致、目力所及,也是一种兴发感动。无论读什么,都读出自己的见解,才是真正会读书了。叶先生将这种方法的运用考证到春秋战国时代,还将之链接到孔子对其弟子的指导,即所谓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,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。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开来,叶先生又提出意大利学者墨尔加利的类似观点,叫“创造性的背离”。“你可以背离作者的原意,有你自己更丰富的联想”,刚刚读到德国的美学家也有类似的说法时,叶先生又笔力一转,指出中国古代从孔子、从《左传》就已经培养出了中国人带着丰富联想读诗的传统。读到此节,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、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对东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信手拈来,印证互通,古今中外纵横开阔,引经据典浑若无意。
再则,通过对“荷花凋零荷叶残”与“菡萏香销翠叶残”的对比,字字精微之中,引出西方文学批评中“显微结构”的作用。语言文字不是名词动词等等的粗浅结构,而是每一个字,它的声音、质地都能起到作用。所以,出自《尔雅》的菡萏就比荷花有距离的美感,香销的声音就比凋零有纤细的美感,翠叶不仅包含了绿,更有翡翠、翠玉的美好。所谓品味,尽在其中。
对多方话语的辨析与尊重
叶先生认为,中国的小词尽管可以让读者产生自由联想,但联想是有基本规则的。联想不是毫无节制、妄说臆说,而是要指向提升人生的修养。这样的基本认识,也迁移到了她对多家学说持有的态度上。例如,王国维认为温庭筠的词只是外表华丽,而清代词学批评家张惠言却认为温庭筠的词是非常丰富的。对此,叶先生并没有妄加评判。她认为,这是由于两个人评说词的方式、衡量词的标准不一样。王国维是从“显微结构”的作用去看的,是逐字品评语言的韵致的,而张惠言的角度则属于“语码”的作用,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寓意的联想。由此可见,王国维有王国维的道理,张惠言有张惠言的道理,角度不同罢了。叶先生的解说不偏不妄,对不同观点兼容并蓄又深入体察,胸襟、眼光兼备。
由叶先生自己的眼光看去,又是一番天地。她认为韦庄的五首《菩萨蛮》是要一口气读下来的,温词则可以拆开来看。因为温词没有整体生命,而韦词是有整体生命的,不看全不足以懂人生。但无论如何,叶先生对王国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,“一生以追求真理为是”,尽管有时代的局限,有知识的局限,但王国维“忠实于自己,也忠实于读者”“不说自己不懂和不知道的话”,真正的治学之道如是。
植根于深厚底蕴的独到见解
如叶先生所言,读古典诗词要有古典修养做基础。修养越丰富,体味越多样。就以“目成朝暮一雷峰”的“目成”二字为例,叶先生引出《九歌》,引出“天水碧”的典故,乃至于“缱绻夕阳红”的心情,所谓“词之言长”,短短七个字就有说不完的意味。所谓“词之雅郑,在神不在貌”,一首词的高下,不在外表,而在精神境界。在对《人间词话》的深入考究之中,叶先生还提出了“双重性别”和“双重语境”的概念,在具体的语境中,必须考量作者身后的整体环境和背景。由此及彼,将古典修养与词之一字融会贯通;由表及里,梳理表象与内在、语境与背景,非具深厚底蕴所不能为。
全书结尾处,仍是回到问题的原点,词之特质究竟当如何定义?叶先生将沃夫冈·伊赛尔的观点翻译为“潜能”,以此概括和陈述自己的观点,一首好词应该有一种“潜能”,既可以通过象征或符号的作用体会,也可以通过语码的联想或语言的结构来体会。想来叶先生是从象征和内涵的角度来选择并定义的。但依个人的看法而言,似不若叶先生书中所提到的“情致”二字更为妥帖,或者说更具韵味。当然,只是管窥之见。
“要眇宜修”是王国维先生对于好词的评价,源自《九歌》。形容深微幽隐之美,精致修饰之美,用作形容叶嘉莹先生的修为和文辞,当不为过。


